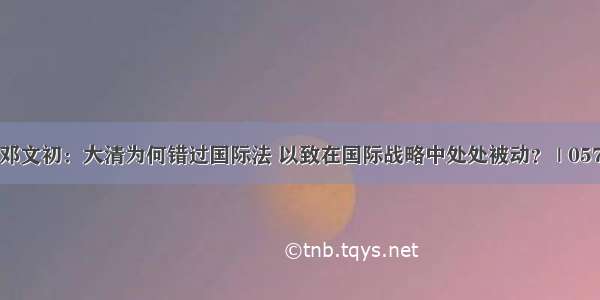文/邓文初(史学博士)
世界近代史为何由欧洲主导而非中华帝国?这一问题几乎成为所有现代史家、社会思想家们的考题,全球史、区域史以及一般近代通史都在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尤其是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历史上中华帝国的强大形象慢慢浮现,这一问题也就更具挑战性。它不仅涉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也触及东方世界的民族情感与自我定位,当然,它更触及到人类的自我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规划未来世界的某种思想资源的重新梳理。
《葡萄牙帝国在亚洲》一书强调,葡萄牙人在亚洲创造的贸易繁荣,并非凭借他们自己的意志完成,而是“受惠于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葡萄牙人控制的环境”。也就是说,作为外来者与陌生人,他们所进入的“主场”并非是依据他们的意志自由塑造的,相反,作为“客方”的他们多少受制于主场规则——“中国海的不稳定形势起初阻碍了他们在这一贸易中获得实质性的利益,直到倭寇危机被解决了之后(葡萄牙人充其量只在其中起到边缘作用),他们才收获贸易的回报”——换言之,葡萄牙之所以能在东方世界中立足并获利丰厚,与其说是他们“殖民”的结果,不如说是东方世界为他们创造的机会。由此,作者提出“伟大的远东转向”这一说辞,认为中国和日本沿海政治形势的变化,为西方世界打开了大门,推而广之,则可以说,近代以来西方的崛起,从根本上说是东方世界丧失了主导权的产物——而中华帝国原来是一个老牌的海洋帝国。
东方世界的衰落,与其从海洋退出有关,是中华帝国自己放弃了海权,而依据海洋战略家马汉的说法,放弃海权的国家必然会走向衰败。
“东方主场”
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则历史学要追溯的是,“老牌的”海洋帝国究竟拥有怎样的海洋意识?16-18世纪的“东方主场”,究竟又发生了什么?
确实不可否认,近代以前的中华帝国曾经主导过亚洲大陆及海洋,日本讲谈社出版的“中国的历史”系列中,由上田信所撰写的明清部分,就使用了书名《海与帝国》,“海洋帝国”之名几乎走红。最近出版的欧阳泰《1661,决战热兰遮》更是热闹,这本书有着一个煽情的副标题“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欧阳泰是美国哈佛学派中著名的叙事史学大家史景迁的弟子,这本书亦继承了史景迁叙事史学的特长。尽管“热兰遮之战”根本说不上东西方的第一次战争,也说不上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早在此前中国与葡萄牙人有过多次交手,且一直都是中方胜出,15屯门之战、15西草湾之战、1548年朱纨发动的双屿港之战及1549年走马溪之战,欧阳泰书中只略提一句),但通过欧阳泰的描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某种认知,那就是,至少就明清之际而言,中国海洋军事力量对于欧洲具有压倒性优势:当时中国洋面仅国姓爷的海军人数就达15万之众,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军队,比荷兰军队多出十倍。
欧阳泰说:“1661至1668年间的中荷战争,是欧洲与中国的第一场战争,也曾是欧洲与中国军队之间意义最重大的一场武装冲突,此一地位直到二百年后,才被鸦片战争所取代”。
在《决战热兰遮》中,欧阳泰还描述了福建海商的伟大事业:
这些福建商人每到一个地方,就在当地建造住宅与寺庙,许多人也选择在海外定居下来,在1500年至1945年的欧洲殖民期间,住在亚洲海外的闽人比欧洲人还多,实际上,即便在欧洲殖民地里,闽人也比欧洲人多。郑芝龙的一个舅舅就住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距离福建约一个星期的航程,郑芝龙到了澳门后与他同住。
华侨与海洋贸易史家王赓武曾将中华帝国海洋力量的消长变迁划分为四个阶段,他认为,至少在第四阶段(1368年之后),中国已经具备在国内外取得贸易繁荣的几乎所有的前提条件:国内需要发展海上贸易;资金盈余,可以用于风险投资;借贷和金融机构已经确立,虽然还缺乏保护措施;航海技术先进,政局稳定等等。
热兰遮城(今台南市安平古堡)鸟瞰图,约翰‧芬伯翁约绘于1635年。
王赓武还指出,当时的中华帝国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这支舰队由官方船只和私人船只构成,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适合航海的舰队。14世纪末的大明海军拥有3500艘适于远洋航行的船只,包括1700多艘战舰和400艘用于运送粮食的武装船,当时,世界上任何海上力量都无法和强大的中华舰队匹敌(参见王赓武《华人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王赓武说,“至于西班牙人,闽南人与之相比所占多大优势甚至更大些,菲律宾群岛就在近旁,中非之间的海域畅通无阻,闽南人在数量上又远远比西班牙人为多,而且,西班牙人处在一个庞大的帝国较弱的一端,更受到抱有敌意的葡萄牙人和摩洛哥人船队的制约。在吕宋的闽南人社区倘若不去主宰政治经济事务的话,按道理应该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这种局面并未出现。恰恰相反,被中国官员遗弃的闽南商人,选择了侨商这种低姿态,面对西班牙帝国的势力,他们孤立无援,许多人实际上沦为西班牙人扩张的工具。”
这些观察出自华裔学者们笔下,或许难免有着某些民族主义情感的影响,但西方学界对于当时中华帝国海洋力量的认知,甚至或有过之。荷兰学者梅林克·罗洛弗茨就认为,由于中国海商控制了万丹等许多市场的中介贸易,更由于他们深入东南亚乡间进行零售收购与销售,中国海商建立了从产地到消费市场的商品营销链条,并始终控制着东南亚至中国内陆的物流网络,因此,欧洲海商只能是在这一框架及其规则之下才能立足,分占利润与开拓新的领域。也就是说,西方贸易网络从一定程度上是东方贸易网络向西方的延伸。
即使是在帝国以禁海为主的海洋战略控制下,中国的海商还是具有巨大的势能。西方势力在进入东方世界时,尽管武装力量及航海技术相对而言占优势,但在16世纪前后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并非占有绝对优势,直至明末,中国海商几乎掌握了东南亚地区主要的贸易网络,这也是西方史界认可的。
海权的争夺
一些西方学者强调,在16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势力能够进入东方,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的印度洋至太平洋西岸海域出现了权力真空,这一真空正是中华帝国退出海洋留下的。如美国社会学家珍妮特在其《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中提出:印度洋区域内的势力范围依据地缘势力及季风环境构成三个圈,其西部由穆斯林控制,东部由中华帝国控制,而中部地区却是印度的势力范围。但到14世纪后半期时,这三种力量均出现衰败,尤其是随着中华帝国退出,整个印度洋区域出现了权力真空,葡萄牙人等西方势力的崛起正是基于这一机会。
明代的大型帆船
她还引用乔杜里的说法:在葡萄牙人于1498年到来之前,这里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试图有组织地控制亚洲的海上航线和远程贸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帝国主宰过一个整体的印度洋及其各个部分。
这些说法真的能解释近代以来决定全球政治格局的东西力量转圜么?
事实上,葡萄牙人进入的区域并非权力真空,毕竟东方世界有着成熟的文明与贸易网络。在葡萄牙等西方人进入印度洋之前,华人就已经在这个领域有着十分频繁的活动且掌握着主动权。西方人来到东方,不仅面临着大明帝国官方的强大制裁力量,同时,他们更需要与无处不在的中国海商打交道。如果海权并非仅仅指主权(那是主权理论成熟之后的事了),则海洋财富的占有,以及为此目的而形成的,对货物的控制、航线的开拓与垄断、商业网点的建设与布局、势力范围的圈定等等与贸易相关的权力,就是海权。如此,则自西方势力进入印度洋及南海区域之前及同时,海权的争夺就已经存在,并随之强化,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权力真空。
《台湾外纪》中提及福建海澄人颜思齐,他曾因命案逃匿日本,寓居长崎,后招纳陈衷纪、郑芝龙等人而坐大,并迅速崛起为重要的海商人物。在其由日本向中国大陆的发展中,颜思齐采纳了弃舟山而控台湾的战略建议——“台湾为海上荒岛,势控东南,地肥饶可霸,今当先取其地,然后侵略四方”——其战略意图就是以台湾为基地向海洋扩张,占有周边的海域。颜思齐以台湾北港为基地,“兴贩琉球、真腊、日本、朝鲜、占城、三佛齐等国,兼于东粤、八闽沿海郡县抢掳”,其“权力”范围横跨海陆,此后横绝海上的郑氏海洋霸权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
《花村谈往》记载郑芝龙海上势力,有如下描述:
凡海盗皆故盟或门下,自就抚后,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从此海岛宁靖,通洋贩货内客、夷商皆用飞黄旗号,联帆望影,无儆无虞,如行徐、淮、苏、常之运河。半年往返,商贾有廿倍之获。
在郑氏海洋霸权下,葡萄牙人以及此后的西班牙人想要进入中国海进行贸易,都必须听从他的号令,遵循他的规矩,荷兰人更是主要通过郑氏集团购买货物,转贩欧洲等市场,这几乎成为此后中西贸易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也造就了一种巨大的国际贸易空间,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记》等记载,1633-1638年(崇祯六年至十一年),每年从大陆载运货物往台湾的郑氏帆船,少则几十艘,多则达一二百艘,有时一个月就有二三十艘。
荷兰人眼中的郑芝龙(穿绿色衣服者)
独占与分享,垄断与自由,东西之间的冲突从其接触开始就颇为激烈,但优势毕竟属于东方主场,海权归属最终也是由主场说了算。因此,当荷兰人以军舰强迫开市时,郑氏集团则以更强大的军力对抗;当荷兰人在海上掠夺中国商船、强征船税时,郑氏集团则勒令他们赔偿损失,返还船、货,退回税金,否则不准通商;荷兰人要到漳州等地贸易,则须征得郑氏集团的特许。显然,西方人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海上力量,而非权力真空。尤其是,郑氏霸权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对西方“客人”,他以贸易对贸易,以武力对武力,以海盗对海盗,始终保持着绝对的主动。
尽管大明帝国在郑和之后确实不再有过那种远征海洋的雄心,也有过从国家层面而言的严厉海禁政策,但这并非就意味着海洋权力的真空。因为在帝国权力之外,中国海商的力量及其对海权的控制,甚至可能比大明帝国的组织化力量更大。
“远东转向”,一个制度比较
如此强大的海商力量何以没能抑制西方势力的进入?何以没有助力中华帝国的海权争夺?尤其是,史界一般认为,西方的崛起与其诸民族国家对海商力量(包括海盗)的利用有着直接的关系。中西之间“大分流”是否可以从这一角度发现某种隐秘的逻辑?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三艘葡萄牙舰船进入琼州海口前港时,海盗施和率领部众进攻,《琼州府志》记载说“佛郎机桅折,避入港”。葡萄牙人寻求大明帝国官方的保护,结果是,琼州指挥高卓统帅官兵及黎族出动,攻击施和,施和设伏,击败官兵。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西班牙人侵入吕宋,隆庆五年(1571年)侵占马尼拉(吕宋在西班牙人占领后改名菲律宾),海盗林凤率舰六十二艘,士兵四千余人,外加妇女一千五百人,由澎湖启程,直指菲律宾。西班牙人紧急动员,组织一支数千人军队反击,双方僵持四个多月。此后西班牙与明王朝联合围剿林凤舰队,《万历武功录》记载:“招番兵五千人,焚凤舟几尽,仅残遗四十余艘,凤不能婴城自守,复走潮。”
西班牙人因参与征剿林凤,获得了明王朝的嘉许,“礼部议赏吕宋番夷”,许其入贡。
对于这些“海盗”史实(更详细的史料参见郑广南《中国海盗史》),中外关系史家张星烺评价道:“明朝海禁尤严,下海者即视为奸民、盗贼,故中国海外势力不伸,以视英国以前收用海盗德雷克以抗西班牙,获得海上霸权者,诚不啻霄壤矣。”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
这一评价确实是一语中的,但背后的原因却需要进一步深挖。何以欧洲国家能利用海盗并由此成功扩张海权,而中华帝国却总是“以夷制贼”从而丧失海上主动?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或许最核心的,还是在权力的分享与分配上。
《葡萄牙帝国在亚洲》一书中有一则“战利品分配”附表:
其中国王占20%,国库占53.3%
余下的部分(共26.6%)依据以下比例分配:
副王占25%
克拉克帆船船长占10%
船长兼领航员占4%
船长占3%
领航员占3%
武装水手(每人)占1.5%
士兵(每人)占1.5
其他占46%。
书中还说,这项规定不仅适用于王家船只的海盗行为,也适用于私人海盗业。依据这项规定,不上交五分之一所得的海盗被称之为alevantados,即“标新立异者”或“自行其是者”,而非“反叛者”。由此,“海盗”不仅被纳入国家管理之内,且与“国家”共享权利。而现代政治史上的所谓“民族国家”的秘密,在这张附表中得到全面呈现:国家并非一个抽象的存在,并非至高无上的主权占有者,而是国王与民众共有的资产,这一资产明细到各自所占份额,有如现代公司制度中的股份分配——而事实上,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欧洲国家在印度洋开拓时,都是以“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现代股份团体为其海洋拓殖先锋(荷兰于1602年合并诸多公司建立“联合东印度公司”),“公司”得国王特许,具有建军、宣战、媾和、发行货币等等特权,当然,其内部的权益也是按照公司法及股份比例分派的。这样,抽象的主权就能换算为每个人的利益,国民为自己而战,而扬帆远征,民族国家从这一角度看,就是自己的国家,这正是“合众为一”的精神所在。
中华帝国的主权概念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仅国土属于帝皇家产,甚至臣民人身也任由帝王予取。帝国的统治就是征服与垄断,任何“染指”就是大逆之罪,这不仅导致官僚机构只能以杯葛的形式对抗帝王私人扩张,臣民个人的谋利无论就法律还是道德而言都是犯罪(原罪),这也是帝国总是将海商逼成海盗,将海盗逼成造反者的体制根源。为了生存,这些备受打压的海商,“实际上沦为西班牙人扩张的工具”(王赓武:《没有帝国的商人:侨居海外的闽南人》《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1期)。
马克斯·韦伯以家父长制概括中华帝国的这种国家形态,在这种国家形态中,官僚体系是接受俸禄的雇佣者,臣民是没有权利的剩余价值生产者,唯一拥有人格(权利)的是君主个人,韦伯认为这是中华帝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阻碍。如此说来,则东西方之间的“大分流”,从西方视角看,确实始于15-16世纪,但并非“远东转向”——东方世界自那位创造“千年犹行秦政治”的始皇就沿着一条变本加厉的家父长制道路行进——而是西方自身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这一历史巨变。
如果觉得《邓文初:强大的海商力量为何未能助力大明帝国扩张海权 | 旧文新赏》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