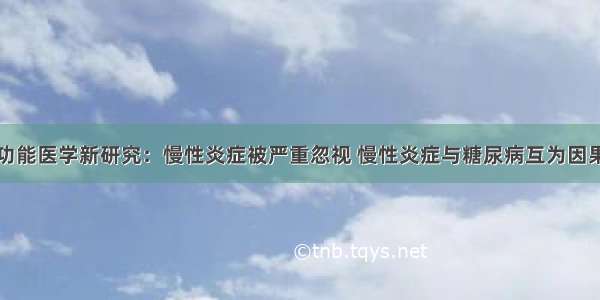作者:李雨轩
近日热映的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由四个故事组成,主要聚焦于不同历史时期两代人的共同生活。四个故事中都有女性的出场,但《诗》中的女性形象与其他三者有较大不同。《乘风》中,乘风的母亲借由话语而存在,表现了对革命的疏离;《鸭先知》中,赵平洋的妻子一开始表现出对丈夫事业的质疑;《少年行》中,小小的母亲也表现出对小小“科技癖”的压制。这三个故事中的女性表现为传统的妻母形象:珍爱孩子的生命,庇护孩子的成长,却更渴望普通、规矩的生活。但《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它以一种女性主义的视角,通过对“长征一号”火箭的燃料雕刻师郁凯迎的生动塑造,重新诠释了“父辈”的概念,挖掘了女性常被忽略的开拓者、引路人角色,勾勒了作为“父辈”的女性的动人形象。
从“以父之名”到母亲发声:“诗”中暗含的父权消解
影片中的夫妻俩——施儒宏、郁凯迎,都是“长征一号”火箭研制的攻坚者,他们为了国家的事业而扎根内蒙古,并在此生儿育女。在工作上,施儒宏负责的是燃料和发动机的配合,郁凯迎则是燃料雕刻师,两人的工作都是工业的、危险的,加之郁凯迎的徒弟也是男性,因此工作中体现不出明显的性别分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男性和女性形象的相似性,但这种相似性主要体现在工作上,在家庭空间中两人的性别差异依然可见:父亲更为活泼,母亲更为隐忍;此外,母亲还要负责做饭等家务。
施儒宏的不幸罹难,迫使郁凯迎不得不承担孩子父亲的职能。她对父亲的死必须保持缄默,又得营造父亲“在场”的假象。她不断写诗,代替父亲表达对孩子的关切和教育。然而,大雨那夜,“父亲”的缺席再难以遮掩,儿子的怀疑和逼问让她深感无力,郁凯迎作为女性的困境由此凸显:一方面,大雨加剧了孩子的恐惧和对父亲的呼唤,儿子的话语强调了母亲和父亲的差异及父亲的不可替代性,她必须安抚孩子的情绪,直面孩子的质疑;另一方面,她是孤独的,丈夫的缺席使她缺少陪伴,她要一个人应付这场大雨。但正是这场大雨,作为一个转折、一个契机,使郁凯迎决心敞开心扉,对儿子讲明实情。
如何让一个孩子理解死亡?这里涉及一个深刻的死亡启蒙、死亡教育问题。当郁凯迎镇定地对儿子说,“我也会死”,她完成了对孩子的死亡教育的第一步,也即借由在场的鲜活生命,让孩子了解、直面人的有死性。之所以借助自己而非父亲,是因为父亲的死非但无法令孩子理解,还可能造成其内心的创伤。但这仅是第一步,更为关键的则是通过片尾的那首长诗:燃料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东西/火箭是为了梦想,抛弃自己的东西/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死亡是,见证生命的东西/宇宙是,让死亡变得渺小的东西……
这首诗概括了影片的主题,揭示了死亡与生命的辩证法,升华了死亡的意义,也从根本上消除了孩子对死亡的恐惧。至此,死亡教育真正完成了。而值得注意的是,就人称来看,这首诗通篇只出现了一个“我”,而没有“我们”,在影片中这首诗也是由郁凯迎诵读的。这意味着写给孩子的诗不再像以往那样冠以父之名,而完全是以母亲的名义写作和传达的。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在拉康后期的“三界理论”中,死亡问题属于象征界,而象征界本是由父性主导的。就现实层面看,在传统的父权社会,只有父亲才有资格对后辈进行严肃的智识教育和思想引领,而母亲则只能承担生养、家务等方面的次级任务。但在这里,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成长教育,并使其进入象征界,恰恰是由母亲来完成的。这既是对家庭领域内传统性别分工的解构,也意味着对父权的消解。因此,郁凯迎实则是用母亲的身份传达了普遍的真理,是母性和父性的综合体;而“诗”也表征着对这种力量和价值的深层肯定。
“父辈”意涵的再审视:重新看见女性开拓者和引路人
在跳出“父亲”之名,直接以母亲的身份向孩子进行死亡教育之外,郁凯迎职业角色的塑造也同样跳出了女性作为家庭支持性而非事业开拓性角色的刻板定位。她主动请缨,对精度进行攻坚。在经历丧夫的剧痛后,她仍兢兢业业地全力工作,充分体现出女性并不囿于传统的性别分工,而是积极追求公共领域的价值实现。
《诗》的女性主义特质不仅凝聚在郁凯迎身上,还散射到子辈身上。《乘风》《鸭先知》《少年行》的子辈清一色都是男性,只有《诗》的子辈同时存在男性和女性,并且在两人长大之后,哥哥反而受到抑制性塑造,是妹妹成了光荣的宇航员,换言之这种传承也是通过女性来实现的。当年那个瘦小、天真的女孩,终于坚定地继承了父辈的意志,见证了父辈梦想的实现。
相较于其他三个故事中男性的“过剩”和女性的“保守”,《诗》具有较强的异质性。这受惠于女性导演章子怡,章子怡在接受采访时说:“父辈不仅有父亲,也包括母亲和我们的师长,以及给予过我们帮助的前辈。”这是对“父辈”概念的全面阐释,消解了其中男性权力的唯一性,也消解了其中强烈的性别指涉色彩,“父辈”被阐释为一个时间性概念,指向引路人、庇护者的角色,他们/她们开拓事业,引领风尚,又教育后辈,提携后辈。以此观之,《诗》的亮点和价值不在于刻意塑造男性和女性的对立,而在于使这种表层的对立无效化,在于构建女性与“普遍”的联系。
我们欣喜地发现,郁凯迎这样的女性形象不仅存在于荧幕上,不仅存在于历史中,也鲜活于当下的现实里。获得“七一勋章”的张桂梅,不正是作为开拓者和引路人的女性代表吗?她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永远令我们钦佩和振奋,给我们鼓舞和力量。而当下的文艺创作也应紧扣现实,努力发掘、塑造、彰显这样的女性形象,不再仅将女性表达困囿于家庭空间,而是更加注重展现其在公共领域所做出的事业和贡献。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来源:中国妇女报
如果觉得《《我和我的父辈·诗》:诠释“父辈”新意涵 再现女性引路人》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